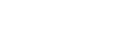主题之中
通常人们批评他的缺席,他轻而易举的放弃,相反有可能的是,一个父亲对功能占有的坚持会产生儿子和女儿的症状。通过对某些治疗的叙述或者轮廓痕迹的穿越,我着手讨论它们带来的结果,并试图接近这个顽固的问题:什么是一个父亲?
换句话说,对于一个父亲来说,跟他孩子的恰当的距离是什么?尤其对于儿子来说,当他表现了一个过度的在场,未来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另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是,这次他作为男人传递了什么?
这就是与大会主题相关的我们的定位,一个原创而且新颖的主题,把我在这个科学的共同体中联系起来的主题:父亲和男人!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承认父亲的功能不是提前就写好的;事后我们必须承认它在切割中或者甚至在其分离的功能中假设了一个准度。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尤其是如果没有跟父母的另外一方一起或者被那一方所表达和性化,这个准度就会有缺瑕。因此在第一个分析上,准度是起作用的第三者,它假设了要去适应和猜测在场的各种张力。然而这种计算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万幸的是生活总是带着它令人惊喜的大奖还有它不同的化身。
讨论
父性的侵入是这些化身的后果之一,尤其当母亲因为多种原因而虚弱的时候,但是也有可能是父性的秩序被他的妻子即孩子的母亲所替换,她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更好地表示反对。当她表达的时候,父性的侵入就会翻译为儿子们要面对的过分,可能是俄狄浦斯问题所囊括不了的。后来拉康有一个经典公式,根据这个公式,分析的企图就是“在可利用他的条件下省去父亲”,具体的说,在那里还是涉及到一个镂空了所有享乐的准度。当然,根据被精神分析的框架、设置所支持的不同模式,这个准度是被分析家和分析者所分享的。有所保留的是,分析的活动,难道它不也是服从于一个准度的吗?
从那里开始,也许就有了在表现为父性功能的准度的东西和我们也可以用分析的活动来衡量准度的东西这两种情况间的平行或者是交流。虽然它们之间首先是远离,我们还是可以建立起一些交流。
通过这个切面,这就是我要抵达问题!
我们还记得弗洛伊德曾经强调就分析这一面来说教育作为职业的不可能!
(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必须重新找到一种母性功能和母性力量的组合,我认为前者尤其是武林科特那里的珍贵的精神的安全感,后者则可以观察到的是父母双方都可以去实施的功能。)
情况一
为了给大家关于拉康这个公式的第一个说明,我在自己的经验中找出一个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翻译的分析,他在一个关于阿拉伯语言的评论中指出这种语言在最近的这些年里有非常重要的变化,适应了短信、博客、电邮等语言。这种变化在与本来是重要和持久的方言的阿拉伯语的关系上,就像是对父亲的谋杀。谋杀部分地解释了由于一些变迁导致的阿拉伯社会的近期变化原因,因为变迁总是从这个语言内部的工作开始的:在阿拉伯经典语言中所背负的难道不也是拉康公式的问题所在:在可利用他的条件下省去父亲?
考虑到主体所有的假设所有的呈现都伴随着变迁,有时候是创造新词。我们注意到在很多环境下,创造新词获得了力量去表达一部分主体无法翻译的东西。我想到了阿贝德拉缇夫·柯西胥 的电影《躲闪》。该片汇集了一帮郊区的年轻人,人们通过让他们演法国经典喜剧大师马里沃名作教他们说法语。结果这些人发明了动词化的“气氛”表达一种引诱的氛围,从而给出一种表达方式,比如:“气氛一个女孩”!
拉康也是某些新词的作者。这些新词翻译了弗洛伊德的非常父性化的理论内部的一个小小革命。革命支持了被拉康操作的移置,一个围绕在话语和语言这个对子上的理论的重组。拉康这个关于父亲的公式如此天才,就好像模拟了这种莫比乌斯带上的不放松其对象而实现的翻转一样!
当我们凑近仔细观察,会发现分析的工作的确是非常丰富的。直接引用一个分析的语法来说,那种不恰当的形式、空间和经验就好像不完整的;这种精神分析体现出来的有限的客观化甚至这种模棱两可都是分析领域中作为构建和解释的受益方,当然还有分析过程中需要描述的其他经验。
我们的目的,即试图接近父性功能的分析活动,带领我们去质问作为分析活动的假设的享乐的中断,为了使一个听见冒起来,甚至直至误解,换句话说通过这些拉康自己的这个享乐概念,就主要扮演了一个分离的角色;在享乐的基础上,是一种实体,一种造就了词与身体的真正的实体;这种实体,当它被中断的时候,一个分离就发生了,那么尤其在精神病人那里就重建起思考的官能,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分析的活动,它也是要做分离,难道不是跟一个父性的功能很接近吗?
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在实践中深受精神病人世界的影响,对我来说似乎是朝向包括了神经症的所有的分析的实践。拿一个近乎粗陋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问题。一个女人面对了一个侵入性的确很强的父亲而没有来自母亲那方的可能的反对,母亲常年面对着她的伴侣一会在场一会消失的既定事实,而这个女人对她的父亲和男人都保留了一种令人憎恨的形象;父亲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阴影笼罩着家庭,当他回来以后又化身为侵略者激起女儿的恐惧。这个男人,少言寡语,行动就像个暴君,永远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他的辞说里,没有任何事任何人在他看来是顺眼的;他贬低五个女儿,当她们稍稍表现出任何一点女性的迹象他就把她们当作妓女。女性性被他用所谓的道德秩序早早地压抑和诋毁,而他本人却毫无道德可言。这个女人,是他五个女儿中的第四个,今天即将四十岁的她对所有能体验到的感性的东西都表现冷淡,除了一个领域,那就是萨尔萨舞。她每周都会去跳好几次,在她看来似乎是因为她不缺少陪跳的骑士。然而这个“萨尔萨”言说着,这个词本身在我看来在法语的回声中好像可以包括了她童年的能指:那个房间!房间,这个词实际上属于她多次听到的父亲的辞说。
这个能指在她身上的复活就好像是父亲内投的回音;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但是通过萨尔萨这个词,我相信了这个典型的享乐实体的表达是以语言的方式居住在人类那里,在分析的工作中就假设了要切断、分开或者还要再抓住享乐,把它编入清晰可辨的支持物上面。在这个意义上,分析是一种在享乐实体上的调查。而关于这个病人,不管怎样她都无法和一些事情分离,无法和作为男人的父亲和解,或者从反面上看男人也是她可憎的父亲!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在这里给她建议为了最后与男人们共舞,就不要把男人同洗澡水一起倒掉,或者停止她在身体里面所携带的战争!
理论
因为涉及到内投的问题,让我们回到分析的结局和谈论它、理论化它的不同方式和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思考抵达的关于分析方法本身的内投或者关于需要更加具体的东西,经验的内投。在这一点上必须强调这种独一无二的方法的独创性,它在于服从自由联想的冒险,既是首先说服从于或然,突然产生的念头(德)!
分析的效果尤其是接待有关不可预料的东西。在分析的进程中,通过或然的反复出现的体验,这个接待有很少的防御性质。一个停止总是伴随着一个悬念出现,或然结构化了基本动力,也就是说,在分析的设置分析的框架和被讲的内容中存在着一个张力,被讲的内容是对以不同的翻译形式效应∕主体出现的等待:分析的框架结构性地重新生产了能指∕所指的二元,但是在一个运动和一个动力中,它们来到之外,允许了对功能的清理。在把这些功能赋予父亲或者赋予母亲之前,它们在对这种方法的使用中找到了一种现时性,这种天才让我想起拉康说过,分析是一种懒惰的艺术。懒惰,意思是说它工作,而由分析者带来的一些效应是归因于这种方法,但作为经验接收方的分析家的积极并不是必须的。
实际上它通过有利于自由联想的语言和转移而发生。就转移而言,除去精神病的情况不谈,它典型性地涉及到重新生成一种转移的神经症,这看来是矛盾的,它的登录就好像是一种穿越了不同精神冲突的增加,又作为这些冲突的范式呈现出来。因此分析家的姿态必须是从一开始就提前了结尾!
就我来讲,我相信一种突出了经验性的对事物的理解。这是基础性的,而且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比如对沉默的操作,在那里分析者从一种在场的亲切感出发衡量效果。我相信不管这次经验是被一个过度在场还是由于一些不适时的干预所毁坏,分析家都必须有所保留。这个艺术的和谐性容不得迟疑犹豫。关于转移,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弗洛伊德本人不就强调了关于节律、机智和对祖先信仰的等待吗?
创造性与所有话语的陈述内容,在分析的领域中,它与使用一个乐器的事实相似,因为陈述内容首先是陈述性的。我们每个人都记得,弗洛伊德说,当分析者正在组织他的思绪的时候,分析家的任何一个不适时的干预都会引起不可根除的恐慌的危险。因此,根据美国精神分析家科特·勒温的公式,只要是在分析的设置中,那么内容的自由则来自于程序的固定,我相信必须理解这种程序的固定就像一个倾听所有间隙的机会一样!从一个形式的固定开始,通过可以支持这个间隙的事实,这个公式强调了在间隙里面起作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精神病的临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不在这里对精神病的工作做过多的阐述因为它导致一个特定的工作,但仅就支持间隙、未知、分析家的被假设知道和这些情况导致的所有替代而言对于多种精神病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和精神病一起,就是在一种替代的病理学当中。
但是,从那里开始,不必走到我们面对的精神病人的扭曲,一个孩子所面对的侵入现象已经可以在一些脆弱的时间里被理解了。它穿越了一部分童年,就像一个留下痕迹的事件,也可以给他造成一个无法根除的恐慌。武林科特说一个孩子有多么依赖就有多么敏感,但是这个侵入也像Schreiber谈论的那样,是灵魂的杀手,孩子不一定记得住它,但是如果这段早期经历引起一个疯狂的恐惧、一个分裂的恐惧、一个崩溃的恐惧的话,那么就需要在成年时期重新演绎、重新解开这段经历。
情况二
现在我想给你们讲两个治疗。至少它们中的第一个可以进入到武林科特的图示下。这个病人分析工作的长期性令人印象深刻,因为我是他第三个分析家。需要注意的是,前两个分析家,一个是比利时的同事另一个是法国同事都有相同的名字但拼写不一样,这个固定必要地将父姓凸显出来。这个固定唤起的是精神分析相遇的偶然性吗?还是在这些相遇中真的存在偶然?显然我不这样认为,你们会理解到,这种固定唤起的是这个分析者的问题。
我们暂不赋予这个延期太多意义,对于我来说,这个病人身上存在着一个主题的固定,是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的,为了进入到这个主题所涉及的中心,该病人在历时多年的所有分析中只谈论着他的父亲!当我说他只谈论他的父亲,是别无例外地关于他的父亲和父亲的教育体系,很少提及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或者他的工作,除了一些他在外国生活的时候所体验到的快乐时候。在意大利、美国,那里借助于说话语言的改变,他重新找到了话语的另一个空间。这让他解脱。试想,这个法国一重要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现在他退休了继续着他的分析,将会在分析中渡过他积极生命的最重要的东西,却无法从他的对象他的父亲那里脱离开来,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吃惊的事情!
当然不管我怎样询问自己关于这个病人的结构,我提及的东西也是某种我不能确定的东西,他那里的分析难道不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的地点吗?简单的说是一个精神病吗?主体在那里支撑了他的真理,但我们也可以说支撑了他的姓。在那里也存在着不可阉割,它不能与这个陈述内容的地点分离,那里不知疲倦地涉及到他的父亲和他、他和他的父亲。然而这个病人两年前爆发了一次心肌梗塞,中断分析的间隔对于他来说是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他提前结束了病后休假,并纠缠他的心脏病医生让他回到分析中来,为了重新找到这个话语和抱怨之地的永久性。这种殷勤的询问,尽管它不少见,而作为停止一击的梗塞所唤起的只有身体可以回应,这样的事情更不少见!
然而,要必须放开这个父亲的过度焦虑是令人担心的。对于这个父亲来说,一个在每个孩子那里的选择性真理意义上的完整倾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不可能谈论的父亲,不可能打开哪怕是一条缝的隐私之门,他给孩子们在了一套缺乏人性的相当严厉的体系中树立起他的教育,通过使用一种跟在他的企业中一样的权威语言。
在这个故事中使人吃惊的,是一个最平常无奇的俄狄浦斯的图示。在家里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五的他,在弟弟也就是家里的最小一个出生之前的五年中,他跟母亲有一个田园诗般的关系。由于小弟弟的出生,他就被送到别处去居住,他说从那开始,对他来说是一个怪物的噩梦代表着他存在的转折点。于是他完全否认了迫不得已的“断奶”,认为他母亲放弃他不是因为小弟弟,而是为了嘲讽父亲的体系!通过把他扔到一个虚弱的地方,母亲又把他暴露在父亲的凶狠之下,他感到母亲的双重的背叛,于是他抱怨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没有一个分析家成功地缝合了他的伤口。在第一个分析家那里7年,第二个分析家那里8年,他对父亲的控诉丝毫没有缓和。没有哪个解释真正地起了作用,他沉溺其间的愤怒或高或低。当然,我们可以说起一个癔症的结构,但是它不能满足面临了一个无法“去主体化”的父亲的过度个案的理解。极端的能指、创伤的代表,父亲同时是这些,在根基上他是一个迫害者。我们接近了让·雅克·卢梭的问题!
难道我们不是在处理一个妄想狂吗?前人说它治愈不了,只要缓和下来就算不错。然而,如果是一个妄想狂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在父亲身上的一个妄想状态和在他的孩子身上产生的效应的妄想状态是毫无区别的。这种过度质问了由父亲导致的空间上的饱和,就像是词的占领,以至于儿子只有在人们讲其他语言的外国才会舒服一点。只有亲缘性在机智占主导的分析活动和激起了苏醒的父性功能既一个不施加强力的他者之间,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是侵入还是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模型的研究。
情况三
现在为了结束,我希望讲讲一个9岁时失去了他的母亲的男人,他是家里的老幺,因为比他年长的兄弟姐妹都渐渐离开了家所以只有他跟父亲单独相处。他母亲的去世是在她因住院导致的长期缺席之后,在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上又因在她去世后不久一个跟他分享房间的兄弟也因车祸在美国的死亡而愈演愈烈。
当这个男人不得不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跟父亲面对面的情景下相对的时候,他的身上唤起的典型特征是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绝对的无能。本来可以弥补这个双重悲剧的祖父母也是缺席,这更让这个房子里面的这种特殊的对话雪上加霜。实际上,回荡着的是一种持续的刺耳、一锤定音的决定、不可预料的任意的怒火,最后又是一个父亲在场的过度。这次因为儿子那里明显的不适,父亲无法支持他的位置,父亲和儿子都需要某种治疗,由于他的无力他不得不在沉默中和自卫里面避难。后来,这个男人在与一个女人的特殊关系中重新发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她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具有癔症性的性格。她在各个方位上急切地寻找石祖,从而产生了由于童年期父亲的关系占据优势而导致的同样的混乱。
如果男性的问题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父亲那里的石祖,那么这假设了在某种程度上父亲的确既可以给出症状也可以接受症状。这种被接受的瑕疵相当于阉割,以一种普遍的方式我认为既是说比如父亲不表现出放弃的迹象,他不实施一种无意义的全面的在场,即他只不过发出了一些毫无意义又无效的噪音而已;说到底,石祖不属于任何人,它是绝对不可能被发音出来的。因此欲望的矢量必须在“什么是一个女人”的谜题中给他现实,造成爱的情形,另外男人可以承担起男人的条件,首先是作为在男性未知数的客观化的不可能被支撑起来之后。
这种非现实和非客观化同样也在精神分析的活动中在分析家的在场、缺席中被找到,后者被拉康减缩为术语:客体小a的位置,即是说没有的客体。如果它存在的话,那么就是作为毁掉分析者工作的那个人。这个分析家的去石祖化,这种假装的工作,这种玩耍躲闪的方式而不是把分析家具体化,与一个男人必须为了拥有石祖而放弃成为石祖极为相似。我们找到一个类似于提及过的公式“在可使用它的条件下省去父亲”的莫比乌斯带的论证。
结论
通过清理三种父亲位置的结构性分析的亲缘关系,并通过归于分析活动的分析任务:分离、机智或者非侵入最后是支持一个“什么是一个男人”的不可能的客观化,它回来传递了一个阉割,仅有的条件是为了一个儿子的生活能够作为男人被支持。
(翻译:姜余)